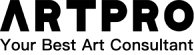專訪 | 陳高傑:我是一個旁觀者,但並非完全抽離於這個世界
萬一空間於2023年9月8日至11月6日推出陳高傑& 特奧多拉·阿克森特雙展“金色獅子”,本文為萬一空間與藝術家的原創訪談。內容由萬一空間整理,經受訪者校核。
陳: 陳高傑(藝術家)
曹: 曹元琪(萬一空間共同創辦人)
曹:最近準備新展覽「金色獅子」壓力大嗎?怎麼個大法?
陳:大,腳痛。

曹:繪畫創作對你來說是一件快樂還是痛苦的事?特別是你的創作過程和其他藝術家很不同,前期需要很多建構,像是空間及場景搭建。我長時間和你在一起工作,我也能感受到前期的架構對你來說是消耗比較大的。在這種情況下,你為什麼還是要選擇以這種複雜的前期架構來創作呢?
陳:我應該說這只是我其中一種創作方式,我身後這張作品《層岩叢樹》就沒有經過特別嚴密的構造,它是一點點生長出來的。再例如這張畫《行走嬉戲》,我先是為自己設定了一個宏大的場景,隨後在裡面斟酌著填充各式人物、符號元素和故事情節,每天都在思考如何增刪裡面的意象和線條。

陳高傑Chen Gaojie
65 x 100 cm
木板油畫Oil on Wood Panel
2023

陳高傑Chen Gaojie
90 × 146 cm
木板油畫Oil on Wood Panel
2023
曹:就像是作品自己生長出來了?
陳:對,這就是兩種不同感覺的創作方法。這兩種方法我都會交替進行,不會說是用了一種感覺就放棄掉另外一種感覺。 「強建構」和「自然生長」的兩種方式都有各自的特點,「自然生長」的畫面會有種自由感,在採用這種方法時,我在繪畫過程中會感到很舒暢;「強建構」的畫作則是在創作完成後才會比較鬆一口氣,感覺很有趣和開心,有種搭建了一座迪士尼樂園或很精密的公園的感覺。但建構過程確實很痛苦,彷彿是工程師在搭建房子時,需要一直觀察造型是否美觀或結構有沒有問題,並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快樂和痛苦是一個比例關係,也不簡單是因為創作本身,生活之中也有很多使人快樂或痛苦的元素,例如身體狀況也會影響我的創作。
曹:最近感覺你身體不太好,這對你的創作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陳:如果是身體原因導致有幾天不能創作會讓我比較焦急,但我同時也知道焦急的情緒對養病來說是更為不利的,這就比較矛盾。
曹:這種痛苦的經驗會直接影響你的繪畫創作嗎?
陳:產生焦慮的情緒之後再投入創作過程中,我會有想要嘗試新技法的心態。比如說,我生病之前是在按部就班地繪製現有作品或準備開始新的創作,但病好之後,我可能會思考是否有新方法來處理這個作品。比如說這幅畫,我在一開始的時候很認真的把高塔滑梯巨像等等造型都安排的很清楚,但隨著繪製進展到一半,我覺得比較放鬆的狀態也很好,我就開始跟著用筆和思想的節奏處理人體,煙跡,天空和山巒,這讓我有了不一樣的心得體驗。包括我以前上大學的時候,就比較受到英法浪漫主義繪畫傳統和講究筆勢、肌理筆觸的傳統技法相結合的影響;畢業後的幾年中,我開始在畫面中加入一些帶有北方文藝復興線條感的風格,而現在這兩種感覺開始融合,還有新的東西正在加入和形成。人,可能是我自己,在處於不一樣的心態時就會想出新的辦法,產生一種新的心態改變。

陳高傑Chen Gaojie
90 × 146 cm
木板油畫Oil on Wood Panel
2023
曹:像這種身體狀況變化的情況,會投射在你創造的人物之上嗎?
陳:這種投射一直都有,我身體狀態好的時候也有。
曹:你怎麼看待這種投射?
陳:因為我看到的世界就是這樣的,我接觸到的現實社會、網路訊息,或身邊人也好,大家都有遭受苦難,當然也有人在愉悅地生活。我從生活中體驗到這些東西,然後每時每刻都會思考將它們融入我的作品裡去。
曹:是一種旁觀者的視角嗎?
陳:我不會像一個非常寫實的寫實小說家那樣去深入地觀察人的情緒和人性的細微變化,因為我並不擅長於此,這並非我的創作強項。某種程度上確實可以說我是一個旁觀者,但我並非完全抽離於這個世界,而是以另一種方式旁觀——我時常在路上行走時就開始與外界信息融合,這些外界的信息在我體內自然地循環消化,在這種情況下我會陷入個人的心流中,逐漸抽離變成一種行走卻不看路的專注狀態。
我在創作中有時也會產生這種狀態。當我把內外的各種訊息融合在一起時,這些內容轉變成了我作品的一部分,觀眾可能會在畫中感受到有抽象的自我存在。例如我之前的大畫《春夢無眠宮圖》裡面的大部分人物和情節可能和我本人的直接關聯性不大,但可以把這一整張畫看作是我這幾年所有沉澱的思考,想表達和想呈現之物的綜合體現。畫裡的人在快樂、在焦慮、在遭遇虐待或其他各種各樣的事情,這些留於畫面的部分都是我日常所感覺、觀察到的,或者是我內心想像到的。我把這些情緒靈感具象化成各種形象,變成角色放入畫中。因為人是在不斷變化的,不能直接定義陳高傑是個快樂的人還是一個痛苦的人。所以我會採用這樣複雜的方法來繪畫。

陳高傑Chen Gaojie
120 × 72 cm
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
2020-2021
畫裡有時候會出現很多各種各樣的東西。例如這裡類似滑滑梯的彈珠遊戲,這裡彈出了很多人頭,人頭表情裡可見有些是開心的,有些是痛苦的,還有一些看不出來情緒。我覺得畫畫就是這樣,在畫第一遍的時候可能是很開心的狀態,第二遍的時候我可能就變成畫中另一個人頭的表情了,繪畫也就是在這樣一個情緒跌宕的過程中推進。我今天看的電影、玩的遊戲、閱讀的書、和他人的對話、我日常的思考、我走在路上遛狗想到的東西,這些都會讓我突然迸發靈感,然後思考能否把這些靈感放入我正在創作的影像之中。

曹:我發現你特別喜歡看一些東西方志怪類型的書籍,你會如何把這些東西重譯編入自己的創作之中去呢?因為一開始的時候,我就覺得你繪畫像在做導演,這一點和其他人很不一樣,你會在畫之前給每個角色做類似人物小傳一樣的人物設定,然後再進行創作。關於這樣一個類似電影拍攝的順序,你是如何想像出來的?
陳:導演可能也是有很多種的,有的人可能是一開始將故事思考得非常完善再開始進行拍攝,有的人可能是一邊拍攝一邊思考,我可能屬於後者。當然我也會做一些設定,但這種設定不是絕對嚴格,不會說創作一定要完全按照我前期的準備來進行。我的畫基本上百分之百是會進行修改的,並非打了型,做了草圖後就完全按照這個思路來繪畫。通常一到兩個月畫完之後的成品和最開始的草圖有巨大變化,可能是顏色、具體的人物,也可能是一些風景或是建築的處理方式,畫面改變也隨我自己的心境與思想發生變化。

曹:我們當時一直想要找到一個合適的術語來形容你的作品,我們就聊到了超現實主義的概念。某種意義上,志怪題材也是古典的超現實,你有哪些內容是從中西方的神話中轉譯出來的呢?還是只是沿用他們的一種方法論來創作?
陳:不管是西方、東方或某些小眾文化的神話、傳說或宗教,拋開各文化之間的差異時會發現他們其實是有內在共性的。例如撰寫一部武俠小說,幾乎所有的情節設定和人物典型都可以從水滸傳裡尋找到;描述一場人倫悲劇,基本上已有的古希臘神話和莎士比亞的作品都可以作為素材。即使在現代寫作中,人們也是很難完全跳出出這種經驗共通性的。包括中國的神話傳說話本裡也是如此,比如妲己褒姒這類被視為禍國殃民但實際上是被迫承擔的複雜女性形象,還有一些看上去純真無邪但實際上佔盡了所有便宜的人物等,都是在這些神話裡很典型(或說帶有刻板印象)的人物範本。在我的創作中可能也會反覆出現某種符號化的人物形象,透過觀察以前的神話、小說、歷史、宗教系統,或是當下生活中的人物角色,我會發現他們通常都會以某幾種人物範式的套路形像出現。
曹:那我可不可以這樣理解,你其實是個熱衷於分析的人,喜歡將他們分類。這有點像是人類學的一種研究方法,把事物進行分類然後總結共通性,然後再利用方法論得到的結果再重新編譯。
陳:這是我其中的一個興趣點,但事實上我在創作過程中不會很嚴格地遵照這一方式去做,甚至同一個符號在我的畫作之中是會有衝撞矛盾之處的。
曹:比如說?
陳:比如說我設計的黑色臉的符號它出現在了很多地方:他可能會出現在這只煉金術士的手心裡,可能會有三隻眼睛,它彷彿是一種具備壓迫性的標誌,嚴肅但同時很戲謔的告訴觀者,世界中有無數東西可供人觀察。再例如這裡有一個小小的彷彿是小惡魔一樣的形象,他基本上不主動去做一些很主角性質的事情,一般只在旁邊觀看;還比如說場景中有人在毆打別人或者是有人在醫院裡,他就會在旁邊當記錄員,或是在一旁跳舞,或是做其他無關緊要的事。


曹:你感覺這是你的替身嗎?
陳:他是我其中的一個替身,這個戴尖頂帽子的人物形像也是我的替身之一。他通常穿著文藝復興開始流行的領圈,身上則是類似漢服的寬袍大袖。有時候他的臉上可能戴著防毒面具。這個角色是一個綜合的形象,有時可能是裸體的,有時可能穿著中式服裝,但整體上他給人一種肅穆的感覺。

他好像在認真地探討著某個問題,展現出執行某種規則或行使某種結構性權利的特質。這和之前的小惡魔是兩種不同的替身。小惡魔就是一種無所謂姿態的形象,他假裝很認真地做一些事情,但實際上內心已不在此處。而尖頂帽子角色則真正投入某種活動、言說或批判。還有這個黑臉符號,不論是否有腿,它一直高懸於天際,代表某種神性或超越性的顯現,這種超越性有時是解放性的,有時是有壓迫性的,有時候又是輕盈的,彷彿帶有某種詩意。實際上,它與我們現實中對超越性的形而上學理解非常相似。它具備這種特徵,現實世界中的一些所謂超越的、神聖的事物可能具有壓迫性,但有時也會啟發我們的詩意,並提供思考人類傳統和本性的管道。
人類對超越的想像可以同時呈現許多不同特點,包括我常用的胎兒形像也是如此。例如體型比成人還大的嬰兒,還有眼睛裡的胎兒,坐著說法的嬰兒。在各種文化中,嬰兒的形象象徵著新生命,代表尚未出現但即將到來的未來。就例如我正在閱讀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尼采將嬰兒視為最高的存在,從駱駝到獅子再到嬰兒。但我的理解是,他並沒有完全否定駱駝和獅子的狀態,他反而肯定了駱駝和獅子的狀態,因為人們必須肯定自己的過去。只有將這三種狀態合併在一起才讓人達到了超越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嬰兒最終會成長為「超人」。因此我在作品中會強調一個嬰兒的符號。


陳高傑Chen Gaojie
38 x 45.5 cm
木板油畫Oil on Wood Panel
2023
當然,無論是從人類學的角度或符號學的解讀來理解我的作品,所得出的結論都不是固定的。我的作品並不像煉金術插圖那樣與某種儀式強烈相關,其中的元素也並未與特定的文化領域緊密綁定。我在作品中進行的是一種藝術上的、心靈上的自由表達。
其中一些元素,像是那三個在空中奏樂的天使,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他們具體在做什麼。我之前看到一張老照片上有幾個女生在吹奏一個巨大的喇叭,雖然我不清楚她們在做什麼,但我看完之後覺得這個比例關係特別有趣。於是我就對這個形象進行了一些變形,讓他們在空中漂浮著構成三角關係,並透過吹奏樂器來象徵某種意義。

至於塔的形象,它是陽性符號和陰性符號的結合,在佛洛伊德的影響下,人們可能會將塔視為一種具有伸張性特徵的陽性象徵。然而,我並沒有完全接受這種概念,我更覺得塔的形狀有一種獨特的美感傾向。我還在塔的頂端設計了一個陰性符號,並從中長出手的形狀。
在過去,無論是中西方的藝術家,他們通常有一個既定的主題,例如繪製特定的風景畫或中國的宮廷畫,如帝王巡視圖。這些作品通常都帶有各種各樣的寓意,如宗教畫。在西方,尤其是文藝復興前後的作品基本上都離不開基督教、古希臘古羅馬的文化與歷史影響。對我個人而言,我會根據我喜歡的書籍或思想來進行文化上的提煉,例如我之前提到的尼采,這並非說我完全認同尼采的思想,因為他自己都沒有完全弄清楚「超人」這個概念到底蘊含著什麼意義,然而這恰好是他的魅力所在。就像我畫的這個黑色小太陽一樣,有些人可能覺得它很像托馬斯小火車,那麼我就說如果你認為是那樣,那就是。當然,如果你覺得它是中世紀那種邪惡的太陽,那也可以,甚至你可以有任何其他的解讀,我的作品開放給多元的解讀,混沌對我來說也是一種重要的傾向。

曹:我們回憶一下剛才提到尼采的內容,你覺得從嬰兒這個符號上你能感覺到什麼呢?
陳:它表現的是一種誕生,一種未知。同時它也很脆弱,代表著需要我們好好保護它。它的單純不含善惡之分,而是代表一種可能性,這正是我最喜歡的地方。然而,我們也常常忽略嬰兒最深層的一點,即這種胚胎其實代表了共同體的傳承,我們常常認為嬰兒是無限變化的,但事實並非如此,它的基因包括行為模式其實已經帶有了前人的訊息,甚至可以說包含了整個人類進化以來的特徵共通性。那麼,嬰兒如何生長成為一個新的生命、一個新的意志、一個新的存在,這是一個很令人著迷的議題,嬰兒生命中那些來自古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元素非常吸引人。
尼采在寫《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以及其它許多文章時,最喜歡的文體之一恰好是聖經體。他表達了上帝已死的觀點,但他自己卻喜歡用聖經體來寫作,這展現了他自身的一種衝突。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尼采自己意識到了這種衝突,例如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他經常大聲呼喊自己只是一座橋樑,真正的超人尚未到來。
如果只單獨看《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而對尼采的生平一無所知,我也會覺得尼采可能快要發瘋了。因為他在作品中呼喚的那種東西,他自己都無法精準描述出來,只能繞著走、繞著描述。西方古典哲學強調的是如何透過邏輯推理或歸納等方法給事物一個明確的定義,他們試圖透過這些方法建構哲學體系,讓任何東西都能站得住腳。而東方哲學,特別是中國的道教或禪宗,講究的不是告訴你真理,而是告訴你可以排除哪些選項,然後剩下的才是真實答案。然而,這個真理到底是誰誰也無法說明白,所以我們只能不斷反推。

38 x 45.5 cm
木板油畫Oil on Wood Panel
2023
尼采在描述超人的時候也讓我感受到他的一種無力感。他總是在說超人要來了,要打破舊有的價值觀,但他自己總是無法達到超人的境界。他給人的感覺就像是超人的一個宣講者,他清醒地意識到即將降臨於西方文明的存在主義危機和虛無主義危機,從現在來看,這種預言可能不僅僅在西方生效,他宣揚的是我們要進入下一個階段,也就是超人的階段,但他並不清楚下一階段具體是什麼。於是這就導致一個問題,他已經掌握了「負」的推理方法,但內心充滿著「正」推導方法所帶來的焦慮。
曹:你剛才多次提到「負」推理的方法,以及尼采的詩性和他的瘋狂相結合,還有他在寫作中運用他最討厭的聖經體,這些你剛才總結的觀點會作用在你的作品上嗎?
陳:我不能說他這是討厭,他對聖經體應該是一種複雜的感覺。這種宗教意識深深根植在尼采的內心以及西方文化之中,但同時尼采自己也意識到了這種文明是會被超越的。我的畫中也有這種感覺,我無法確切地告訴觀者我認為的世界是什麼樣的。
曹:我覺得你的一些隱喻、符號其實也都是在用「負」的方法在敘事,而且你繪畫中有一種很神奇的秩序感和瘋狂感的結合,這種矛盾和反叛感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同樣矛盾的尼采會吸引到你。

陳高傑Chen Gaojie
120 × 72 cm
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
2023
關於藝術家
陳高傑(Chen Gaojie)於2015年獲得中國美術學院油畫系學士學位,現工作、居住於杭州。他的畫作受到耶羅尼米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彼得·勃魯蓋爾(Bruegel Pieter)、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等藝術家的“怪誕畫”的影響,兼容波斯以及臥莫爾王朝細密畫,中國敘事冊頁以及藏地唐卡等研究。他所創作的形像看似是詭譎的、異化的,實則也是藝術家對於童年時期生活山海經、伊甸園式的想像與當下生活場景的變體重現。
藝術家透過觀察生活,閱讀文字影像,和自由想像來做作品中的設定。對於某種元素或符號的選擇、對某些造型和色彩的使用,一方面由藝術家的經驗和喜好決定,另一方面又呈現了歷史文化傳承的集體無意識,生活環境甚至是身體狀況。這世界的各個層面,對藝術家來說都處在一種有待於被認知的狀態中,包括他對宗教信仰,對待神秘主義的態度,藝術家把它們看做是某種不斷進行永不停止的藝術創造,是人類不得不為的一種生存事業,雖無法從真理層面篤信它們,但作為現實的一部分,它們已經與藝術家密不可分。
特奧多拉‧阿克森特(Teodora Axente) 1984年出生於羅馬尼亞錫比烏,碩博畢業於克盧日藝術學院,現工作生活於克盧日-納波卡市。她的媒材以布面油畫為主,而她的創作主題較多涉及當代存在的問題和對人性發展的社會調查。她於2011年獲得埃斯爾藝術獎(Essl Art Award)並參加奧地利維也納埃斯爾博物館群展,同時於2013年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現代藝術館參展等,被稱為羅馬尼亞最受人矚目的藝術家之一。
藝術家在一系列裝置和材料限制下的異化人物繪畫中,探索了內部危機的狀態。阿克森特以獨特的具象語言為標誌,將她的主題設定為一個超現實環境,創造了屬於自己的對立世界,即世界一側是有形的物質,另一側則處於難以捉摸的內部精神中。身為克盧日學院的一員,阿克森特與羅馬尼亞先鋒派畫家團體一同探討了幽深而迷人的物質性對現代社會人們精神層面所帶來的實質顛覆性轉變。
展覽詳情

金色獅子Scène Noire
陳高傑& 特奧多拉‧阿克森特
Chen Gaojie & Teodora Axente
雙個展
Duo Exhibition
展期:
2023年9月8日至11月6日
地址:
深圳市南山區海上世界文化藝術中心2層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