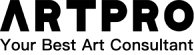“画之为物,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否则直如照相器,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何贵乎人邪?何重乎艺术邪?所贵乎艺术者,即在陶写性灵,发表个性与其感想。” ——陈师曾,1922年
兴之所至,余味无穷。
展览“兴之所至”落脚于“兴”,强调其“余味”。何谓“兴之余味”?这可作多义之理解。一面,这有“兴致无尽”的意涵,如此说来,艺术家在既定规范之外的自然流露,在意外之处按耐不住的性情表达,在闲暇之余玩乐觅得的独到创作,“游于艺”的不拘一格的创作精神,是一种字面意义上的“余兴未尽”;另一面,“余味”之“余”,又含“业余”之意,而业余又绝非贬义,反倒是一种自觉的标新立异。官方与主流一旦框定,或成为追随的对象,便常是一种范式与套路;其反面正是一种业余精神,力求自成一格,卓尔不群。艺术关乎自由表达和批判意识,反官方的业余状态也好,严肃之余的轻松自如也好,都标示着业余的精神气质,维系着一种不落正统的本真天然。
上述“兴之余味”的两面性,也有所统一、有所汇聚。它们的交点,是艺术家的性灵。由是,创作从作品回到了人,从艺术回到了艺术家。陈师曾题引所言,论述的正是人(以及人的气质)与绘画(以及其他形式的艺术)的关系。艺术既是媒介(carrier)——通过她,可观其背后创作者的性灵、个性与感想;艺术同时又是塑造者(crafter)——她是艺术家的呼与吸,是流露也是反照,反哺、塑造着艺术家的心灵。
所以,我们可以说,兴之所至达到的余味无穷,既是一种创作状态,又是一种个性与性灵;既有余兴的游艺,也有余兴之人。艺术的起源,便有游戏之说,讲的便是人在游戏中,摆脱功利,进入纯然的精神与审美世界。这甚至不需要任何专业的训练,而只需要纯真性灵的自然表达。但实际上,维持本然天真的玩乐和自始至终的“业余”,是妄想的,也是难以企及的。谁能不受任何污染,不怀任何目的,赤城地本然与天真?谁又能回到艺术的起点,无视过往艺术历史与视觉文化,自建一片领土?
尽管如此,这样的方向却正是我们希望在这个展览中觅得的。严格说来,展览的主体都是专业的艺术家,不过他们的创作追求中,却集合了诸种“兴之余味”的表达。他们有严肃思考之外旁逸斜出的自然流露,“大家小作”,闲适惬意,不拘一格;其中也有以“玩乐”为核心的创作追求,致力于某种“业余”与“游戏”,比之“艺术品”,创作的结果更像是“玩意儿”;这里有汲取民间资源、试图回到艺术发生的本源之地的尝试,不落窠臼,一派天真;还有对于民间故事的无限演绎,一部《西游》,演变为无穷的故事,幻化出无尽的兴致。
除了专业的艺术家,展览也的确纳入了匿名的创作者,或者说业余的艺术家。这些匿名的艺术家是艺术历史中飘散的魂灵,他们隐姓埋名,留下了无可考证源头的作品。他们来自民间,来自角落,也来自深圳的大芬村……当然,他们并不因为“匿名”或“民间”,而天然地确保其质量上乘,只是我们(不乏主观地)筛选出那些颇为稚拙本然、自然天成的作品,以平等的艺术的名义,伴我们共同走上余兴未尽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