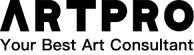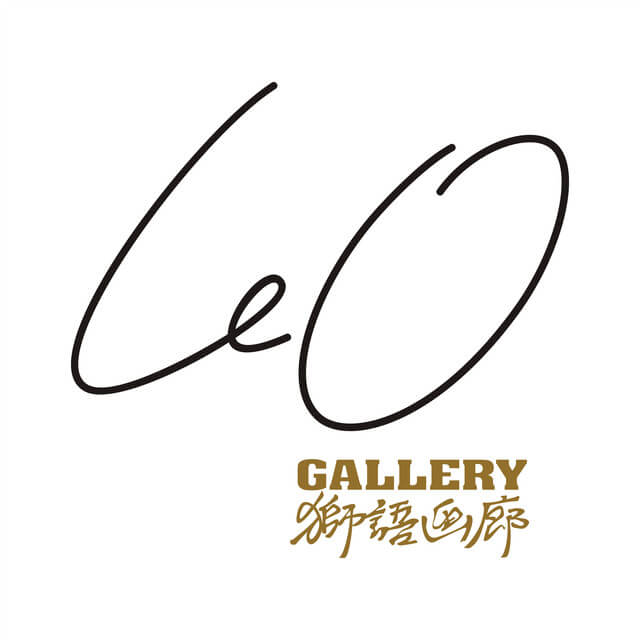临摹与变形
——庞海龙的社会批判路线
文|王晓松
动物尸骨作为材料在丰富艺术表达的同时,也通过对材料自身生命线索的追问强化了当代艺术在社会性批判上的直接了当,典型如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1997年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实施的《巴尔干巴洛克》(Balkan Baroque)。作为曾经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以及一度被卷入欧洲火药桶的中国,我们大概或许应该能够理解阿布拉莫维奇洗去牛骨血污时的悲情。虽然国际政治事件与艺术之间未必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恰在此时,中国的艺术现场也在经历了“当代”与“国际”引入的初震颤之后,在经历了1980年代创作与表述里诱人的戏剧感后,从主体或艺术史建构而非简单的暴力革命意识逐渐增强,有意识地寻找应对自身问题的方法——不同在于前一时期对世界认识原始的、偏执的狂热,后一时期中得以冷静地思考新一轮全球浪潮中“左翼”思想、在地大小文化传统、日常生活等对包括艺术在内的影响。显然,目前专注于围绕1980年代的艺术史叙述是有缺陷的,原因或是因为讲述者对自我价值的迷恋,或是我们被其语言艺术感染力所迷惑。
庞海龙没有赶上中国当代艺术的1980年代,但是1990年代的大学时期被“后革命时代”的反思所波及,他与大多数中国的艺术生一样,几乎都经历了从材料、形式去理解观念的过程。对有中国传统文化或艺术教育的人来说,这个过程又显得顺理成章,不事张扬而从“身边”的小世界入手理解大千世界,既没有像此前那样的冲动也没有此后移植过来的观念先行;不过,在繁杂的观念信息源轮番轰炸中,大多数人都还是会迷失,说到底,路终究是个人、时代与原生环境等多重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生长于中药世家且有制药厂开办经历的庞海龙,自有他对“材料”与“生命”关系的特别理解,过去十几年间用的材料无论是动物尸骨、灰尘,都与他从生活与生命的小处着眼理解社会的习惯有关,庞海龙以今天的视觉方式为这些材料撰写的“后史”,既是艺术经验的技术积累,也带有个人艺术宿命的色彩。
以牛骨为材料进行的创作与其“大棒”作品在早期是齐头并进的,因语言的日常性使其简单的形式冲突能传递更直接的批判,多少有1980年代的暴力回响,然而在“牛骨”、“粉笔”等作品创作时,庞海龙“识趣地”把自己作为问题,通过美颜术来改造、挑衅或戏弄既有的系统性表达,从still-life到“宅生记”,形成了由关键词向段落、篇章的缓慢展开。但这些作品并没有明确的规划,更多地是艺术家对社会变化的一种应激反应,它们既是同源的,又有内在纠葛。作为这一时期的典型性作品,“隐力”系列从2018年开始,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双双转入“地下”。对比此前挥舞的“大棒”,它显然是对当时诸多社会事件背后的隐藏结构的“临摹”,而“隐力”则是在“临摹”中向社会底层话语及表达权力问题的批判——艺术家以艺术的方式所做社会性“临摹”与17世纪董其昌对古典作品临摹以实现语言再造的“仿”的意义一样,只不过它跳出了艺术形式自洽的小圈层。因此,必不能将“隐力”视为一件静态的“装置”,而要与阿布拉莫维奇对待牛骨那样强行控制情感的精神自残同等视之——所有铺在地上的标准尺寸的牛骨地板都来自庞海龙的手工制作,它们谦卑地铺在展厅的地面,如同所有被利用、被抛弃、被遗忘的生命被人踩在脚下无从发声。在“正常”匮乏的大环境下,想必大家都会理解,相对于肉体伤害,无意识的精神施暴造成的伤害更为永久。
其实,我们作为作品的第三者是无法准确理解和描述艺术家的意图的,尤其是在这类行为作品中,一定有大量被扭曲、被消耗的部分无法完全呈现,它只属于创作者甚至有限的创作时间里,所以需要有渠道提示人们留意那些本应有的愤怒的、绝望的与喜悦的、疑惧的信息。庞海龙的作品并不是孤立的,其他露骨的、不合时宜的作品恰恰提供了晦涩阅读的有效线索,穿过“隐力”的暗门,才能发现隐藏着的生命流转的形变以召唤荒诞形式背后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