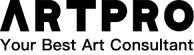在孩子生病前,杨俐每日的工作从准备早饭、收拾打扫开始,爱人九点半起来,那时会再做一次饭。因此,她总在四五点没有琐事时画画,记录前一日的随想,发在小红书,她为自己写的简介是:一位家庭妇女的绘画日记。近半年,杨俐过上了规律的陪护生活:一早给孩子揉腿,等医生查了房,把孩子的床位推到窗边晒太阳,晒足再移回来。下午是这位母亲的空闲时间,她还是每天都画,画架随身携带,在医院时会放在病房的阳台。
杨俐今年46岁,典型的湘女面孔,常以双麻花辫示人。幼时学画未果,青年拾起画笔,中年在油画院进修,没能让她完全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2023年,她开始画斑鸠。第一幅标注了日期的斑鸠画绘在2月1日。有感于窗外大树上的一对斑鸠夫妇和诞下的小斑鸠,杨俐着手记录它们的生活,这一系列就以“老朋友”这个平实的名字命名了。
在5月29日的“老朋友”中,杨俐第一次身穿鸟衣与斑鸠对坐,一人一鸟,仿若熟识,但形同对峙,好像交换了灵魂。这天起,更多的“杨俐”进入画面,斑鸠成了她的绝对拟体,而后迅速笼罩到更多的对象和社会境况:孩子的病情、自身的精神疾苦、生存环境的抑遏、对纯真的怀想——她将对人间事的情感倾注在斑鸠身上。斑鸠成为了杨俐,杨俐逃脱了,得以从恐惧、恼火、无助与焦虑中短暂喘息,这种心灵上的保护适度削弱了现实对一位平凡人的无情摧毁。
与发源自现实的“鸟”并行的是她称为“小怪兽”的奇幻形象——杨俐对幻象的感知似乎是一种必然,她过分敏感的神经能够自动识别出域外之物,这些生物的轮廓在杨俐拿起作画的信封纸时已在纸面,她只是勾勒。它们让人联想到《山海经》中的奇诡异兽,和发轫湘楚山水、远离城市文明的民间夜谭,就像是大禹测绘下九州范围外的“海外”和“大荒”中的精怪,曾在湘人的基因中隐性了几个代际,如今都借由杨俐的笔成形了。
几乎每一幅杨俐的斑鸠、怪兽画,都分毫未彰显过人类在面对自然物时,天然的权威感和改造的欲望。她对形象的塑造先知先觉,由直觉野蛮地脱出,不问秩序。与其说是杨俐用斑鸠拟人,不如说这是自然物在主导人类的罕见情况。杨俐是那条纽带,且相信她更愿被归于自然的那一方。
杨俐与鸟的因缘此前在她的生命经验中已几次浮现,兜兜转转又拾起。儿时返乡路上的布谷鸟叫,乡愁般反复回响;青年时期,在株洲铁路旁出租屋中绘制自画像,她莫名将一只神鸟放进了画面;爱人为她雕刻的鸟形木雕,经过十余年颠沛仍完好地保存。后来在她家中聊天,我们问起杨俐想不想当鸟,她说——
“我肯定啊,不是我想,我本来就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