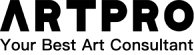当代唐人艺术中心荣幸地宣布,位于北京顺义区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北京)的唐人总部空间将全新开放,并将于7月24日下午4点推出年轻艺术家群展“后我世代:如何书写年轻艺术家”作为开馆展,由陆向怡担任策展人。
唐人总部空间位于北京顺义区金航东路的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北京)。总部空间包括B5号楼的全部6层,总面积近3000平方米。画廊总部负责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北京、曼谷、香港、首尔四地空间的运营、管理和协调。除了按照国际标准设立的展厅空间,总部还同步拓展了VIP展示厅、研发中心、地下储存空间等,满足了唐人全方位协调服务的需求。这也是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在亚洲地区设立的第7个空间。
唐人北京总部空间的展览和活动,定位于对全球年轻艺术家的研究与推广。开馆群展“后我世代:如何书写年轻艺术家”,汇集了18位当代出色的年轻艺术家,在当下的多元趣味导向、媒体社会化和新的数字技术革命发生的此刻,年轻艺术家正在以更加轻松的姿态书写着自我的历史,此展也拉开唐人总部空间对年轻艺术家群体研究工作的序幕。
参展的18位艺术家包括:亚历桑德罗‧吉安尼(Alessandro Giannì,意大利)、陈英杰、李黛伦(Diren Lee,韩国)、江上越(Etsu Egami,日本)、贡坎(Gongkan,泰国)、郝泽成、侯佳男、黄冰洁、吴晶玉(Jade Ching-yuk Ng,中国香港)、贾一瑞、奇蒂·纳罗德(Kitti Narod,泰国)、廖曼、奥利维尔·苏芙兰(Olivier Souffrant,海地)、桑图尔(Suntur,泰国)、王茜瑶、温迪玛格恩‧贝莱特(Wendimagegn Belete,埃塞俄比亚)、杨伯都、张占占。
后我世代:如何书写年轻艺术家
陆向怡
如果存在一本《年轻艺术家史》的话,该如何书写?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冷战和后现代语境中式微的英国艺术家群体制造了“yBa”概念的崛起,这切实影响了全球艺术史进程和书写,至今仍发酵着巨大影响和商业价值。始于2009年的纽约新美术馆三年展(首届的主题是《比耶稣年轻》)也具有某种先验精神和历史野心,年轻艺术家的历史远没有变成一种时尚轮回和短暂的过气,它甚至像一种现实漩涡,强有力地席卷了艺术生态。这不仅是一种“过去史”、更是“当代史”(克罗齐)和“未来史”。令人无法忽视的是,作为“后我世代”的一批年轻艺术家,正以强劲的姿态介入当下艺术生态,不同于强调自我的“我世代”, 后“我世代”的年轻艺术家,展现的是更加轻松的状态,他们对原有的“反叛”流露出警惕与迟疑。历来新的艺术家的崛起都曾借鉴之前艺术家的历史发展经验,在绘画的辗转发展以及新艺术的崛起中,绘画媒介的复苏,新的书写将在这些历史的循环中寻找真实,“后我世代”的一批年轻艺术家的书写方式也会不同。年轻艺术家们创造了消费主义、数字技术革命经过中介编码化的产物,通过“表现主义”“图像一代”等前人后人的的精神传递,找寻更为个体化的表达。他们的绘画大多带有新形式主义手法,充满了与当下现实的互文与无限创造力。
回到克罗齐的历史叙事中:如何区别“真正的历史”(Contemporary history)和编年史(Chronicle),他的回答果断:视其是否具备生命。克罗齐断言,历史是具有“策略”的——使得一本历史书成其为真历史的,正是由于现实生活的需要而激发的对于过去的理解和把握。历史不再是某种理念或多种理念的收集,“历史节点”仅变成了在实践中根据需要而随时调整的步骤。比奠定某种体系化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先让历史发展中的物质性和载体(人和事)能够存活下去,他认为,这是今天史学迫切的问题之一:历史的生命力问题。而“关于年轻艺术家的历史”契合了这种历史考察对象,其为一种“正在发生的历史”,正是这种复杂态促成了这个展览得以进行研究。他们的生命力和必要性在哪里?
存在主义哲学已经解释过“我”和“自我”的历史性:“存在”(dasein)即时间。自我只有在历史和动态中才有意义。如何理解“后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发表于1992年,如果作为一种“后历史人类”考察,这一批“后我世代”创作者生命里并没有经历过常规“历史”中的自我,正像是时间停止后的“冻结生命态”(Historical cryonics)。如果说克罗齐提出当代史才是真正的历史,这也令这一批艺术家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年轻艺术家”(meta-young artist)。目前的情况更像2008年后约瑟夫·格里玛(Joseph Grima)等人曾提出的“后匆匆主义”(Posthastism)运动宣言的某种反复。当时成员之一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描述过艺术重要的是抗拒时间的“均化作用”(homogenization)。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标准化和量化人的时间,而艺术和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创造让人的心理变化能自由地令时间和年代变得更快、更慢或者反复。在这个意义上,新学院派艺术和加速主义并不冲突,新一代艺术家的“自我”能够自由地适应历史诠释,在延续中拥抱未来从而获得新鲜感和持续更新的意愿。
所谓的“我世代”,实际上指的是国内的“泛80后”与西方的Gen Y的一部分,这一代人非常显著的特征是个人主义。但更年轻一代艺术家却展现出社群文化与早熟的职业嗅觉的一面。大多是具有良好的学院基础和多元背景更给予强大的技巧、理论和艺术史知识作为支持。新形式主义绘画以及一些更贴近自身的边缘性社会思考(比如性别、地域、种族)对于这代人而言更具有吸引力,而呈现出一种“低烧”的状态。他们的姿态更加放松,能够轻松地并置60、70后熟悉的“波普艺术”、“图像一代”,以及80后发展起来的“屏幕一代”艺术。当下的多元趣味导向、媒体社会化和新的数字技术革命前提下,艺术评论和价值取舍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品评年轻艺术家的飞短流长也正成为其历史性的一部分。对争议性和多元化解读的创新性理解,已成为当下迫不及待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