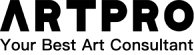一颗花骨朵,在成为影像之前掉落,可能是刚刚,也可能过了一会。和以往的经验不同,花蕾离开了枝桠,却没终止生命的迹象。它在一片落下的花瓣中,反复地跳动,嫩绿和粉红的色泽,依然蕴含着生命的饱满——疑惑也随之而来,没有外力,也失去了给养,它却如此跃动。说“跃动”有些过于欣然,它有点像挣扎,但挣扎又过于悲怆,它不过按着自己的宿命去开放。毕竟,呼吸在艺术之前早已存在。
这是姜杰的《落花有言》中最初看到的意象,也是展览“俯仰之间”的情感写照。
2022年春天,在桃花开的时候,姜杰拍下了这段影像。最初,这个偶然的现象让姜杰感觉有些陌生和惊奇。它着实有些不寻常,从未绽放的花蕾却如此颤动。也是这个陌生的际遇,“不可能”和“反常”让我们脱离了原有对生命认知。
“偶然性”为这件作品赋予了一个重思的契机。它不借助任何外力,却可以如此强烈地跃动。或许,从自然的角度我们可以想象,它试图在脱离枝干后继续绽放。这样的描述,也为这场目击,增添了几分哀伤的色彩。无论是花骨朵自身,还是观者,她们都在这一瞬间完成了一场共情。这场共情,对于满树的花骨朵而言,只是一个偶然性的孤例,它并非花蕾的全部命运。然而,作为观者,当我们将花骨朵的跃动理解为一场挣扎时,它的含义被赋予了人的情感色彩和精神投射,也因为触景生情,人的经验给它一种更强大的挣扎感。
和传统古诗中对于“落花流水”的咏叹不同,这段6分多钟的影像,记录的不是自然中的日常,不是“春风吹又生”般亘古不变的乐观。而是偶然间,花骨朵在一个异常的状态下,生命本身的强度,在逆境中,终究无果,但又重复、执着地跃动。
在骨朵晃动的身姿和镜头的虚焦之间,你很难分清还未舒展的纹路上,是花瓣自身的经脉,还是时间赋予的褶皱。这些足够细微的神经,如今展现在巨大的尺幅中,逼迫并邀请我们去更仔细的观察身边和周围,理解它们的跃动与挣扎,也邀请观者借由艺术家的目光,去参与“落花有言”的隐喻,它要言说什么?它的言说又引发什么样的意象和情感转变?
花蕾的命运总是短暂的,即便它在树上,它的肉身也不过是临时的状态。在它之前,树木经历了一个冬天的沉闷,等待着一场春风,几场细雨,然后冒尖、抽芽,顶破树枝的那层表皮,成为骨朵。然后,也只有几天,它们中一半落下,一半幸运绽放,之后生叶、结果。花蕾,只是它的学名,它的肉身不过是花朵颤变前的躯壳。但赋予它生长和变化的是生命绽放的意志,即便它的肉身坠落,它的“灵魂”仍在俯仰之间挣扎。或者说,姜杰拍下的并非是花骨朵的孤立存在,而是那些不易察觉的,被我们所忽视的感知共性的存在,它们都被宏大叙事所遗忘,一片叶子在水中的沉浮,一颗花蕾在地面挣扎,一场突变对于细微生命的更改,尤其在近几年间,生命的俯仰从未如此真切地在我们的现实中强烈地浮现。
或许,花骨朵自身的意念是我们无法探寻的,但这一场缘分的相遇让姜杰再次去思考:什么引发了创作的灵感?又如何去发现生命中具体的感受?是什么触发一件作品开始的念头,促使一件作品,乃至艺术的产生?是我们掌握的知识,还是生活中闪烁的感知?
对于艺术家而言,灵动、细微的感受,总是先于理论的存在。当一个“灵感”出现时,它起初来自于真实的生活本身,而从来不是知识或臆想的产物。而当它被创作,并成为一件艺术作品时,它又总是携带着艺术家自身对生活的认识。
每一个对事物的观察,都可能带着一个壳。我们往往看到的是事物的表象,而在表皮之下或是之外,有着更多与世界的微妙联系。《无题》拍摄于2017年,和《落花有言》一样,它也是姜杰偶然所得。影像里,墙边的一件雕塑上,泛起一阵阵像是波纹,又像是光晕的水雾。这些不确定的光影,并非源自于雕塑本身,或制作的特效,它只是天窗玻璃上正在蒸腾的水汽,通过阳光洒在雕塑上的镜像。这场偶然性的发生,将一件雕塑作品的所在,引向与外部世界更为丰富的关系,与雨水、季节、天气,或是天顶的一块玻璃,等待着观者与它的相遇,发现并捕捉的目光。
无论是《落花有言》,还是《无题》,一件作品的意义不再取决于自身,而是它与更宽广的世界之间存在的种种偶然性的联系,每一个细节都可能牵连出一个故事。也因此,它的隐喻性和意象,从一瞬间的悸动,一个微小丰富的生命关系,将我们引向更广泛的生命现实,牵引着我们去想象,去连接世界中普遍存在的轻与重、沉与浮。
一件作品在哪里结束?
——这是过往的艺术史中经典的命题。从追求完整理想的古典主义,到残缺之美的维纳斯,关于艺术两种方向的探讨从未中止过分歧。它关乎艺术家对于目的和结果的认知,对艺术所承载的功能、价值、意义的不同的理解与体悟。
《俯仰之间》是姜杰2023年的全新创作,它由5件悬挂的雕塑组成。和经典雕塑中的稳定性和坚固感不同,她并不追求这种永恒的纪念碑性。《俯仰之间》的创作时间足够漫长,经历了反复搭建、修改,原有的结构随时可以被变化、破坏。上一时颇为满意的结果,在下一时成为重新肢解的起点。在这个过程中,姜杰的认知发生着截然不同的变化,它有着自己的变道和流速。当灵感显现时,感知不断改变着作品的方向,模糊的质感、生长的线条、摇曳的结构,闪烁出异样的光晕;当灵感隐退时,那个根深蒂固的完整性经验再次浮起,它怀疑之前的形态,将其视为垃圾。
艺术知识中的“好”,总是否定灵感的浮现,它试图将一切牢固,严丝合缝,逻辑明晰。反复打破,也意味着反复建立。在这个过程中,姜杰刻意留下那些败笔。或者说,她并不相信“残缺”与“完整”任何一个命题,也不会用任何一方做终极审判,而是显现这个不确定的拉扯过程。好与坏、对与错、跑偏与校正,在作品中有着同等的份量,相同的确凿。
感知的变化,又总是取决于观察。对于艺术家而言,观察时,在哪一部分使劲、放大,把那一部分剔除、隐匿,决定了作品的变化。有些时候,创作中的“败笔”会让作品变得更有张力,一个东西的显现,并不取决于自身,而是取决于关系。在和姜杰的访谈中,她偶然间提及中国传统的书法,说到一段精彩的言论:“一个展览,一篇书法,它都是整体的好,而不是局部的好坏。它允许拉扯,草书里允许有几个字差。你单看一块时,它是掉的,是差的。但它整体却是可以的。作品的’对’,并不在于艺术史,而是它自身在关系里的对,在通篇里的‘对’。”
然而,和绘画、书法不同,雕塑无论如何塑造,它都会产生一个实际存在的物。也因此,它的抽象化过程变得尤为艰难,无论艺术家脑海中有着何种不确定的念想,最终总是落点于一个实在、真切的物体。
于是,如何使用材料,突出哪种物质,成了姜杰必然面对的命题。她需要尽可能选择一些身边触手可及的物品,以避免二次翻制带来的难以更改的形态。这些材料又需要符合创作过程的需求,可以随时搭建,临时更改,反复破坏。纸黏土、丝绸、纱布、铁丝、竹签,木棍,塑料的珍珠与钻石,这些材料和它们与生俱来的敏感性,成为创作的主材。与其说是创作的需求,倒不如理解为姜杰选择了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事物,以生活中的轻,替代雕塑中的重;用生活的真实发生,忘记经典艺术中那些趋于不朽的完美面目。
姜杰并未给这组作品设定一个终点,或是到达时应有的样貌。它们总是随着躯壳的破碎,反复更改。有时,雕塑的外沿,像是一个很轻的壳,可以随时从里边飞出来;有时,它又彼此缠绕,你很能分清空间与空间之间的前后关系,像是拉开的肉,重新长出来,薄薄的一层,却连成一片难以辨认的凹凸扭转。然而,当这些复杂的关系,被反复而又肯定地表述时,作为一件作品,它又有着什么样的语义?换句话说,它最终想要表达什么?
我想,在理解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忘却艺术史中那些冗长的主题,知识并不能让一件作品成立,阐释也不是艺术家最重要的工作。观看时,也不要试图将它分类,无需借助那些现成的、格式化的定义。只有这样,你才能看到一个别人看不到东西:用真正的“眼睛”看到蓝色,看到金色的筋脉,看到风中颤动的珍珠,表皮下骨头暗藏的闪烁,看到高处的星空和地面拉长的光影。
总之,这一切感知有着与人相关的气息,无论它丑陋,还是优雅,是终极,还是一念,姜杰的工作即是让它现形,现形它隐匿的样貌,现形它涌动的意识,闪烁的灵感、颤动的感知。但如果你非要,找到符号的明证,你也尽可以,将每一个物像,分门别类的纳入你经验中的想象。
“过程”的现形,拉扯、对错和好坏之间彼此的注视,在姜杰这里尤为重要。《俯仰之间》所显现的并非是明确的故事,而是造就故事的过程,故事节奏、变化与冲突,它是故事转折的奥秘。现实的变化,并不取决于人物、时间与地点,而是取决于发生,取决于它的内部和外部的拉与扯,强与弱、对与错的关系。如同那粒落下的花骨朵,它偶然的命运,就地的挣扎,才能成就它的闪耀。
一件好的艺术作品,总是在“能指”和“可指”之间徘徊。它和这个世界中我们所珍贵的微小事物,有着一样的韵律,它们在俯仰之间,有着和生活、云朵、月亮一样的悲与喜,阴与晴,圆与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