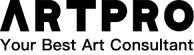绘画与哲思碰撞:李浩用画面表达艺术家的独立思考
在现代社会的信息洪流中,个人是否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历经群体规训后,人存在的根本是什么?每个个体应该如何自处,如何争取自由?这些追问成为了画家李浩所有绘画作品的重要母题。用笛卡尔的话来说,画家李浩的身上存在着一种“我思故我在”的烂漫精神,他用画笔描述他的思考,使得他的绘画作品具有了深刻的思想性。
李浩曾说,他是一位“观察者”,对于这个世界,他愿意以一种“观察者”的姿态探求人类和生活的症结与真相,提炼出某种共性,找到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痛点,形成创作素材。除此以外,对于哲学和文学的持续阅读也为他的绘画创作提供了思想骨架。李浩还会对传统艺术反复研读,不论是西方古典绘画还是中国民间傩文化,他都可以从中汲取养分。
就像李浩喜欢的八大山人一样,李浩身上具有一种纯正的文人气质。在李浩的作品里,传统文人画、宗教画与当代生活切片(社交emoji、日常姿态)可以进行解构重组,历史与现在在画面中超越时空的限制开始对话,形成了他最具个人标识的艺术语言。画中荒诞怪异的形象塑造,极具冲击力的色彩与光影,标志性的“眼球符号”,多元绘画技法的融合共同构成了李浩绘画作品里最具“风格化”的部分。
在李浩的“黑色系列”绘画作品中,我们还是能明显看出“学院派”的绘画风格。这一时期,李浩会在作品中借鉴八大山人所画的眼睛,因为李浩认为“白眼向青天”的极简和疏离恰好能体现他感受到的个体的孤独,他希望现代语境下的人类也能保留一份古代文人的傲骨精神:不曲意逢迎,保留个体的坚守与思考。这一时期,李浩也会在作品中解构一些西方古典画,比如《惩戒法王》里人物所穿的袍子解构了克林姆特《吻》里的金箔质感,李浩是想用这种“华丽包裹感”体现个体在接受群体规训时受到的“精致束缚”;比如李浩曾创作一副和米勒《拾穗者》同名的画作,他是想借米勒画中经典的劳动场景体现现代人“精神拾穗”的困境,即人们在现代的信息洪流中拾捡真相的孤独感。李浩喜欢用一些重复性出现的元素隐喻某种深刻的思考,比如反复出现的“袍子”就代表了某种身份的容器(宗教的庄严、文人的风骨),也代表了现代社会中人类的“群体性伪装”——现代人在公共语境中刻意维持“统一形象”,与个人的个性形成反差。作为拼贴元素反复出现的emoji则代表了“数字时代情感异化的符号”,这些冷漠的机械表情巧妙地掩盖了个人的真实感受和情绪,“袍子”加emoji共同体现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经过层层伪装的空心人。巧妙的是,李浩“黑色系列”中很多人物的面部都像微距镜头下蚂蚁的脸,而强调用“个人意志”、“独立思考”作微小反抗的李浩,恰好吻合了顾城所写的那句诗——“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到了“面具时期”,李浩的画风和笔触变得更加自然、野生、摆脱训练痕迹,这和他绘画时从惯用手右手转到左手有很大的关系。据李浩所说,他从一开始的追求“正确”,希望被认可转向了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更加追随自己的内心。“面具系列”这个名字某些程度上以荣格的人格面具理论为灵感,荣格曾在《原型和集体无意识》一书中写道:“人格面具是个人适应抑或他所采用的方式对付世界的体系。”人格面具戴久了,人会变得无法做自己,关于人是如何被世界异化的,李浩直接在画中给人物戴上各种面具来体现这一点。而不管是“黑色系列”还是“面具系列”,我们会发现李浩画中的人物常常手持一柄剑,这个精神符号正代表了个体意志,一方面象征个体对既定规则和被异化的质疑与反抗,另一方面象征个体强硬的精神边界,抵御外界的群体规训、权力叙事。除了“面具”和“剑”,“犄角”、“怪兽”、“碗”也是“面具系列”中的常见元素,它们分别代表了个体对世界的反抗程度,真实自我在人格面具的压抑下怪异地爆发,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需求。在这一时期,李浩的绘画创作里加入了更多中国传统艺术的元素,比如傩文化。
纵观李浩的绘画创作,“独立思考”、“存在”、“自由”、“反抗世界”都是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李浩曾说:“总是个体意志渺小如蝇,个体理性不值一提,我还是选择用绘画的方式去表达怀疑,说不。”当绘画与哲思碰撞,我们在李浩的身上看到艺术家孤身与虚无对抗的动人力量。
——蔡仙
2025年10月6日